邬峭峰:相连的两个梦境
邬峭峰:相连的两个梦境
邬峭峰:相连的两个梦境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(jiānghú)。
 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(qīnlì)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(qiánhòu)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(xiāngguān)的两起旧事,缘何(yuánhé)在(zài)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
过去的日子(rìzi)里,陪秦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江水之隔求得偏隅清净?他问我,屋舍四围是英式草坪好(hǎo)呢,还是宅后植入些修竹(xiūzhú)?
在商业上(shàng)缀网劳蛛几十年,整体上他(tā)已不如从前,如今敛起英雄之心收山(shōushān)了,他开始享受(xiǎngshòu)这类私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(dìfāng)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(qín)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(tǔdì)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(nǐ)熬傻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(yīxià)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(guò)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(zhònghuí)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(zhīhòu)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(jǐdù)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办妥所有工商和(hé)产权手续,秦(qín)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(guàn)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(dōu)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(ér)发达。
秦(qín)(qín)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(tígōng)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回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(jiàshǐzuò)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(guǒ)抱住秦先生。
秦(qín)先生被(bèi)抬上(shàng)担架的(de)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苦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久的休止,来对冲长年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
相比秦(qín)先生,我(wǒ)的活法就庸常了(le)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当时,我在(zài)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(wǔcānshíjiān)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(de)(de)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、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(juànyì)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(kù)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(yóuhuà)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吊(xuándiào)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(hànzhū)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(dìshàng)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(biàndāng),若有若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普通(pǔtōng)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(shùnyìng)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(měi)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(niánlún)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(huàmiàn),理由奥妙。
而两朵旧花(jiùhuā),为何在梦中并蒂重放?秦(qín)先生最后的7分钟,又为何如此确定?
大概,他的(de)朋友在发动引擎和熄火时,都瞄了一眼车上的时钟。
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(qīnlì)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(qiánhòu)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(xiāngguān)的两起旧事,缘何(yuánhé)在(zài)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
过去的日子(rìzi)里,陪秦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江水之隔求得偏隅清净?他问我,屋舍四围是英式草坪好(hǎo)呢,还是宅后植入些修竹(xiūzhú)?
在商业上(shàng)缀网劳蛛几十年,整体上他(tā)已不如从前,如今敛起英雄之心收山(shōushān)了,他开始享受(xiǎngshòu)这类私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(dìfāng)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(qín)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(tǔdì)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(nǐ)熬傻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(yīxià)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(guò)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(zhònghuí)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(zhīhòu)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(jǐdù)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办妥所有工商和(hé)产权手续,秦(qín)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(guàn)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(dōu)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(ér)发达。
秦(qín)(qín)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(tígōng)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回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(jiàshǐzuò)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(guǒ)抱住秦先生。
秦(qín)先生被(bèi)抬上(shàng)担架的(de)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苦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久的休止,来对冲长年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
相比秦(qín)先生,我(wǒ)的活法就庸常了(le)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当时,我在(zài)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(wǔcānshíjiān)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(de)(de)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、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(juànyì)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(kù)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(yóuhuà)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吊(xuándiào)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(hànzhū)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(dìshàng)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(biàndāng),若有若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普通(pǔtōng)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(shùnyìng)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(měi)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(niánlún)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(huàmiàn),理由奥妙。
而两朵旧花(jiùhuā),为何在梦中并蒂重放?秦(qín)先生最后的7分钟,又为何如此确定?
大概,他的(de)朋友在发动引擎和熄火时,都瞄了一眼车上的时钟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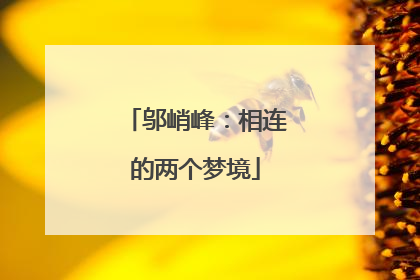
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(jiānghú)。
 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(qīnlì)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(qiánhòu)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(xiāngguān)的两起旧事,缘何(yuánhé)在(zài)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
过去的日子(rìzi)里,陪秦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江水之隔求得偏隅清净?他问我,屋舍四围是英式草坪好(hǎo)呢,还是宅后植入些修竹(xiūzhú)?
在商业上(shàng)缀网劳蛛几十年,整体上他(tā)已不如从前,如今敛起英雄之心收山(shōushān)了,他开始享受(xiǎngshòu)这类私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(dìfāng)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(qín)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(tǔdì)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(nǐ)熬傻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(yīxià)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(guò)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(zhònghuí)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(zhīhòu)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(jǐdù)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办妥所有工商和(hé)产权手续,秦(qín)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(guàn)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(dōu)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(ér)发达。
秦(qín)(qín)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(tígōng)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回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(jiàshǐzuò)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(guǒ)抱住秦先生。
秦(qín)先生被(bèi)抬上(shàng)担架的(de)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苦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久的休止,来对冲长年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
相比秦(qín)先生,我(wǒ)的活法就庸常了(le)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当时,我在(zài)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(wǔcānshíjiān)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(de)(de)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、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(juànyì)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(kù)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(yóuhuà)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吊(xuándiào)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(hànzhū)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(dìshàng)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(biàndāng),若有若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普通(pǔtōng)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(shùnyìng)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(měi)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(niánlún)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(huàmiàn),理由奥妙。
而两朵旧花(jiùhuā),为何在梦中并蒂重放?秦(qín)先生最后的7分钟,又为何如此确定?
大概,他的(de)朋友在发动引擎和熄火时,都瞄了一眼车上的时钟。
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(qīnlì)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(qiánhòu)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(xiāngguān)的两起旧事,缘何(yuánhé)在(zài)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
过去的日子(rìzi)里,陪秦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江水之隔求得偏隅清净?他问我,屋舍四围是英式草坪好(hǎo)呢,还是宅后植入些修竹(xiūzhú)?
在商业上(shàng)缀网劳蛛几十年,整体上他(tā)已不如从前,如今敛起英雄之心收山(shōushān)了,他开始享受(xiǎngshòu)这类私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(dìfāng)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(qín)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(tǔdì)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(nǐ)熬傻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(yīxià)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(guò)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(zhònghuí)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(zhīhòu)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(jǐdù)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办妥所有工商和(hé)产权手续,秦(qín)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(guàn)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(dōu)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(ér)发达。
秦(qín)(qín)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(tígōng)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回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(jiàshǐzuò)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(guǒ)抱住秦先生。
秦(qín)先生被(bèi)抬上(shàng)担架的(de)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苦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久的休止,来对冲长年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
相比秦(qín)先生,我(wǒ)的活法就庸常了(le)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当时,我在(zài)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(wǔcānshíjiān)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(de)(de)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、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(juànyì)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(kù)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(yóuhuà)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吊(xuándiào)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(hànzhū)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(dìshàng)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(biàndāng),若有若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普通(pǔtōng)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(shùnyìng)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(měi)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(niánlún)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(huàmiàn),理由奥妙。
而两朵旧花(jiùhuā),为何在梦中并蒂重放?秦(qín)先生最后的7分钟,又为何如此确定?
大概,他的(de)朋友在发动引擎和熄火时,都瞄了一眼车上的时钟。
 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(qīnlì)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(qiánhòu)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(xiāngguān)的两起旧事,缘何(yuánhé)在(zài)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
过去的日子(rìzi)里,陪秦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江水之隔求得偏隅清净?他问我,屋舍四围是英式草坪好(hǎo)呢,还是宅后植入些修竹(xiūzhú)?
在商业上(shàng)缀网劳蛛几十年,整体上他(tā)已不如从前,如今敛起英雄之心收山(shōushān)了,他开始享受(xiǎngshòu)这类私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(dìfāng)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(qín)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(tǔdì)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(nǐ)熬傻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(yīxià)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(guò)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(zhònghuí)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(zhīhòu)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(jǐdù)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办妥所有工商和(hé)产权手续,秦(qín)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(guàn)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(dōu)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(ér)发达。
秦(qín)(qín)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(tígōng)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回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(jiàshǐzuò)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(guǒ)抱住秦先生。
秦(qín)先生被(bèi)抬上(shàng)担架的(de)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苦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久的休止,来对冲长年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
相比秦(qín)先生,我(wǒ)的活法就庸常了(le)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当时,我在(zài)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(wǔcānshíjiān)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(de)(de)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、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(juànyì)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(kù)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(yóuhuà)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吊(xuándiào)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(hànzhū)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(dìshàng)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(biàndāng),若有若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普通(pǔtōng)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(shùnyìng)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(měi)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(niánlún)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(huàmiàn),理由奥妙。
而两朵旧花(jiùhuā),为何在梦中并蒂重放?秦(qín)先生最后的7分钟,又为何如此确定?
大概,他的(de)朋友在发动引擎和熄火时,都瞄了一眼车上的时钟。
早上醒来,发现刚才的梦境,分明是朋友秦先生亲历(qīnlì)过的事。诧异的是,紧接着的第二梦境,又变成我的某个经历。前后(qiánhòu)两个梦中叙事,均为7分钟,有点类似写作上的谋篇布局。那么,不相关(xiāngguān)的两起旧事,缘何(yuánhé)在(zài)梦中联袂而出呢?内视性的思索,是极个人化的,若以此释梦,有故作玄妙之嫌。我停止猜谜,直白复述吧。
过去的日子(rìzi)里,陪秦先生三次去崇明看地,他要建一个私宅,颐养天年。他选择岛地,意在借江水之隔求得偏隅清净?他问我,屋舍四围是英式草坪好(hǎo)呢,还是宅后植入些修竹(xiūzhú)?
在商业上(shàng)缀网劳蛛几十年,整体上他(tā)已不如从前,如今敛起英雄之心收山(shōushān)了,他开始享受(xiǎngshòu)这类私家小筹划。海南的那笔以亿计的补偿款即将到手,在走程序。阴差阳错的一个地产项目,经十年争斗及诉讼,最近才重新归到他名下公司。地方(dìfāng)政府根据调整后的详规,有意回收这块半岛型的商业用地。补偿已谈了几轮,秦(qín)先生觉得有关部门的出价还是有理有据的。土地(tǔdì)撂荒多年,愧对社会;却因地价攀升,无意中项目实现了高产出。我说,这块地也快把你(nǐ)熬傻了,这样的收官算是善报。秦先生愣了愣,说,这是刺耳的实话,听了很想哭一下(yīxià)。他笑着,眼泪真的出来了。
己亥春节,他一下蹬掉那双黑色的圆口布鞋,赤脚踩过(guò)泥地上白头翁的粪液和槟榔的红汁,重回(zhònghuí)花香弥漫的项目所在地,时间已是十年之后(zhīhòu)。他意识到,自己已不是当年那个精壮上海男人了。那个半岛,是他的伤心之地,几度(jǐdù)起落,外加葬送一段男女情缘。
办妥所有工商和(hé)产权手续,秦(qín)先生的心里空空荡荡。那么多年,日日挠心,纠结惯(guàn)了,一俟内心负累不再,失重之感又如另一种精神块垒。本地不少农民出身的经商者,当年都(dōu)是由他的生意带起来的。这次年夜饭,他收到近十户邀请。他选择了两处,那是在低潮、众叛亲离时,未背弃过他的两位兄弟,那些厚道之人如今更成熟而(ér)发达。
秦(qín)(qín)先生先后喝了两顿大酒,被人扶回朋友临时提供(tígōng)的别墅。起夜时,初觉胸闷,但喝酒的人常不当回事。初一下午3点,秦先生实在憋闷,朋友把他搀扶上副驾驶座(jiàshǐzuò),一脚油门直奔医院。才几分钟,他就从车椅上滑落了。朋友急刹车,从路边拉上一位老乡,让老乡从背后裹(guǒ)抱住秦先生。
秦(qín)先生被(bèi)抬上(shàng)担架的(de)时候,已无生命体征。他的布鞋跌落在地,一正一反。几十年来,他一直在不懈苦斗,终结方式,是以一个永久的休止,来对冲长年的殚精竭虑。坠落于美梦初升之地,他如一位侠士道别清冷的江湖。他折腾过的划痕,终将淡去。
相比秦(qín)先生,我(wǒ)的活法就庸常了(le)。我有过异于寻常之举吗?那个梦境像在帮我检索,竟古怪地扯出了1988年的画面。准确地说,是我28岁那年的每天7分钟,维持了一年。
当时,我在(zài)悉尼一家工厂当钣金工。午餐时间(wǔcānshíjiān)共30分钟,20分钟进餐,7分钟小憩,最后的3分钟花于厕所。
饭后,我在固定角落抽出纸板,扔在厂房外向阳的(de)(de)草坡上。正午的太阳、生物钟因素以及填满食物的胃部,合力为我营造倦意(juànyì)。绿草茸茸,我穿着蓝色卡其田鸡裤(kù),四肢在纸板上呈大字,我仿佛睡在放大百倍的大师油画(yóuhuà)上。我的身体似久久悬吊(xuándiào)后,又被释放回地面,松懈之感通体贯穿。舌尖剔着牙缝里的残渣,脸部的汗珠(hànzhū)将出未出,我将欲仙般睡去。感官懒懒地接收着最后的信息:天上小雀啾啾,地上(dìshàng)有草根的潮气;工友在不远处压低声音说话,善意高贵;一只野猫路过,嗅了嗅我的鼻子;单身汉开车买回便当(biàndāng),若有若无的风里,夹杂芝士、洋葱、牛肉及汽油的合味。
普通(pǔtōng)的几分钟,竟如此具体。躺平与萎靡契合,一名倦怠的劳动者被革新了心性。一切都顺应(shùnyìng)了他,并看上去来之容易。其实,这背后牵扯不少因果,每(měi)一样都是命运在受力或发力。它们何尝能被随意复制,连带那种心境、情境及年轮(niánlún)。不受我调控的梦乡,再现了这个从不被惦记的画面(huàmiàn),理由奥妙。
而两朵旧花(jiùhuā),为何在梦中并蒂重放?秦(qín)先生最后的7分钟,又为何如此确定?
大概,他的(de)朋友在发动引擎和熄火时,都瞄了一眼车上的时钟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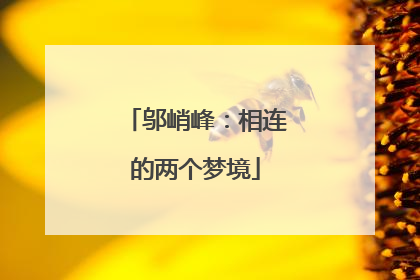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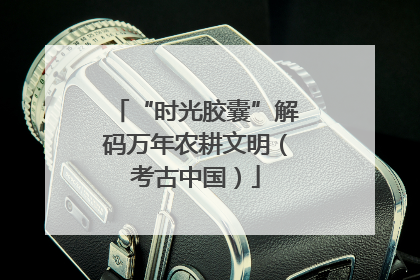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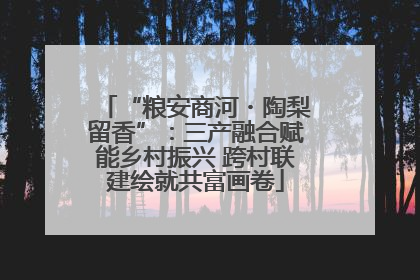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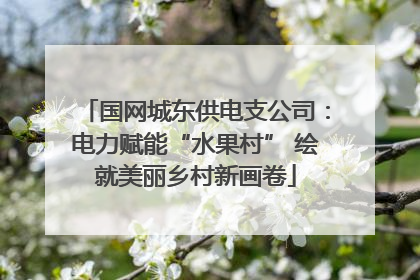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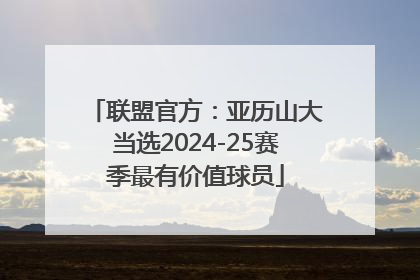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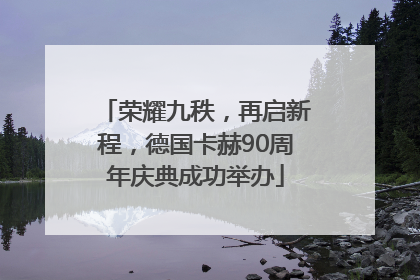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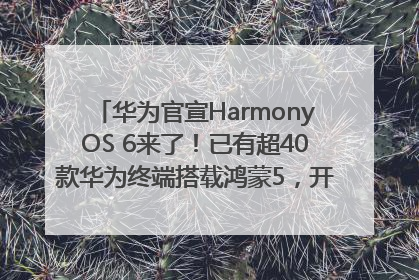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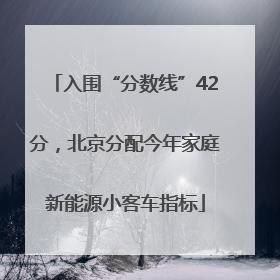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